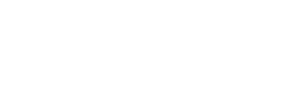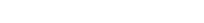【科研戰“疫”(六十四)】
過去的一周,對國人來說,是值得欣慰的一周。這一周内,不僅大自然的春天悄悄到來,而且,新冠肺炎“戰疫”的春天也珊然而至:國内疫情進入清零階段,在武漢這座“英雄的城市”,疫情也迎來量級的實質性改善,新增确診病例持續進入個位數,“盡快清零”的夢想已從“遙不可期”變為“觸手可及”。從全球來看,情況卻大不同。自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以來,coronavirus疫情成為過去一周内全球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雖然各國都在呼籲國民不要恐慌,但事關重大,人們的恐慌情緒還是持續攀升。美國股市有史以來一周内兩次熔斷,充分體現了民衆和市場對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和自身安危的巨大擔憂。
國别雖然不同,民族雖有差異,但在巨大的自然災難面前,作為同住地球村的“村民”,其情相連,其理相通。近三個月以來,衆多受病毒傷害的同胞和“逆行者”以鮮血與生命的代價,在這場不見硝煙卻殘酷無比的戰争中得到的經驗和教訓,應該是為人類帶來的無價貢獻。這不僅是未來我國各地流行病防疫的寶貴财富,也應該被其他國家借鑒和參考。
第一,強大的國家能力是我們經受住嚴酷生存檢驗的根本依托。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可以粗略地的理解為國家有效地采取措施促進集體性行動,以實現既定公共政策目标的能力。比如疫情防治,這無疑是一項規模龐大、錯綜複雜的公共品供給政策,涉及千家萬戶、傷及男女老幼,任何一個私人個體都無法單獨完成,必須要由政府部門、民衆、各類組織等國家的多層次行動主體通過協調一緻的共同努力來實現。顯然,重大疫情不僅是對政府的考驗,更是對我們整個國家無選擇性地打擊。也正是我們擁有了強大的國家能力,才使得我們國家的治理體系彰顯出了卓著的優越性。已有文獻将國家能力定義為“國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強制能力。也有學者将國家能力簡化為财政能力與司法能力。嚴格來說,國家能力包括了政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但不完全等同之。在這方面,我同意周其仁教授的觀點,不要簡單地把“國家”簡單地等同于“政府”。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我們的國家能力有着多重的行動主體。首先,黨中央明确了清晰的防控方針,并通過總體部署、科學決策和權威影響為疫情得以有效控制提供重大政治保障,中央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引領着整場戰“疫”的正确方向。其次,各級黨政軍機關節假日不休、緊急行動、全力奮戰。第三,各企事業單位、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與廣大人民群衆萬衆一心、衆志成城、團結奮戰,全力投身于疫情防控的人民戰争。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千千萬萬醫務工作者主動請戰,義無反顧地“逆行”向疫區,連續奮戰在“戰疫”鬥争第一線,用生命踐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信念。第五,各級黨員、志願者、社區工作者等優秀中華兒女,捐款捐物,勇于擔當,忠誠地繼承和發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綜合來看,在“戰疫”鬥争中的國家能力,不同于太平時期的國家能力。疫情中的國家能力,首先的保障目标是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在這個特别時期退居其次。這充分體現出了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也正是當前部分西方國家疫情失控的制度根源。客觀地說,中國的疫情防控模式确實值得推廣,但其成效是以我國強大的國家能力為首要前提的,這不是每一個國家可以輕易模仿的。這對大部分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是最大的挑戰之一。
第二,有效的治理體系對打勝防疫戰争至關重要。治理(governance),可以簡單地理解成當事人為實現共同目标而采取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也可以解釋為隻要當多數利益相關方接受才會生效的規則體系。正如一句名言指出的,“沒有秩序就沒有治理,沒有治理也沒有秩序”。治理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上至國家層面的管理活動,下至企業組織的管理,以及公共領域事務的管理,隻要多個人在一起共同努力完成一項活動,就會涉及治理問題。新冠病毒疫情對我國的防疫治理體系是一次沒有先兆的突然襲擊。從應急管理的角度來看,一開始的早期階段,我們做得不夠好,在應急物資、信息披露與溝通、保護機制等方面存在着明顯的短闆和一定程度的混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實來講,病毒疫情對社會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因此,其治理體系不是單一的經濟治理或社會治理機制所能勝任,而是有着非常強的綜合性特征。防疫治理體系需要政治治理、政府治理、公共衛生治理、醫療服務治理、社會治理與市場治理等多種機制協同發揮作用,還涉及跨行政層次、跨行政部門、跨區域協調治理等問題。這麼複雜的治理體系,很容易出現責任界定模糊、政策目标不明确、協調困難、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導緻各種治理失靈現象。在近三個月的防疫鬥争中,我國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鄉村社區等,通過封城隔離、明确政治責任、建立聯防責任等措施,從人員、機制、信息、制度、政策等各個方面逐漸理順了防疫治理體系,構建了系統的激勵機制。實施過程中,上級政府抓部署,下級政府抓落實,依法堅決查貪治庸、杜絕表面文章,有力保證了政策與制度的執行,為防疫鬥争提供了重要驅動力。
第三,因地制宜,腳踏實地,尊重科學構建有效“戰疫”體系。新冠病毒可謂是一場人類猝不及防的自然災難。在自然災難面前,科學比政治更為關鍵,綜合知識比單一學科更為有效。不同區域,區情不同,疫情不同,需要因地制宜,制定針對性強的有效方案。歸納過去近三個月的“戰疫”實踐和教訓,科學“戰疫”是否出成效,取決于如下幾個因素:一是構建疫情監測的長效信息系統。依據這類系統,可以及時獲取疫情本身嚴重程度的準确信息。這些信息包括新發傳染病的性質、傳染性、緻死率、可治愈性、發生時長等,構建有效的傳染病報告機制,及早系統掌握這些信息,對及早啟動防控至關重要。二是推進防疫體系的落實水平。傳染病防控的根本在于“三大關鍵環節”——控制傳染源、阻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這些措施看起來非常簡單,但落實起來其實非常之難,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使政策執行者和人民群衆對傳染病的快速形成防範能力和防範意,提升防疫體系的及時落實水平。将簡單的事情做紮實,就是講科學,就是執行力。三是提升治療能力與科學研究水平。對于傳染性強、發病突然的傳染病,建議國家将其列入國家能力培育範圍,盡快整合關鍵治療資源與科研資源,集中攻克病毒分析、藥物提煉、臨床治療等環節的關鍵技術,盡快形成有成效的治療方案。此外,加強對病毒與傳染病領域基礎研究工作的支持,理應成為我國需要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戰略。四是明确政治治理理念。在“戰疫”的實踐過程中,真正影響決策成效的決定性因素,應該是國家治理的政治理念。顯然,越是重大的疫情,其防控體系的涉及面也就越廣,決策也就越發複雜。在落實“三大關鍵環節”過程中,就需要平衡公共健康、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越是嚴格的防疫措施,涉及的區域範圍可能越廣,需要平衡的利益主體也就越多,帶來的經濟損失也就越大。因此,能否擺脫個别官員以主觀猜想代替理性分析,能否從“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角度出發、遵照科學規律來有效防疫,就取決于決策者的政治理念了。本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黨和國家,毫不猶豫地将人民群衆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真是國之幸甚,民之幸甚!
(石軍偉 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教授、博士生導師)